贾府末世有何寓意?你看明清时期这个时代背景!
周玉琪2019-01-07 11:26

文/雪月溪
艺术的再造,不能超越生活本身的范围。哪位作者能把他本不熟悉的生活写好?哪一位作者能把他自己本不熟悉的人物写的活灵活现?谁都不行!
《红楼梦》的作者,当然也不例外,书中的各个角色,他们各自所本照的生活原型也不会是各个角色本身。
打个比方罢,有人叫你给你太爷爷立传,可是你根本连他的面都没见过,你根本对他的任何情况都并不了解,不得平空想象,虚拟虚构,胡编乱造,你还能咋的?大不过,就是把你生活中熟悉的一些人的事迹,移在你的笔下,深浅随意,任你点染描摹刻划而已。

作者所本照的生活原型,并不是角色本身,实生活与艺术,彼此间有所出入,就觉得不对,就认为“这不符合事实”?那宋江可是宋江?吴用可是吴用?鲁提辖就非得是鲁智深本人?
如果没有对生活最深刻的了解,那么在你的笔下,你所塑造的各个人物角色,他们是不是一个个都能够丰满起来?
艺术的再造,并不是生活的重现。生活中的任何一段经历,任何一种事实,反应在文人笔下,也各不相同,但也不是完全不同。它们都是既有相同的共性,也有各不相同的个性。有共性有个性是一切事物的本质。《红楼梦》和《红楼梦》本身的事实,是不是可以例外?

我们现代人读了《红楼梦》,众人各自都有所反应并且表现各异,清代的人们读了《红楼梦》没有反应?或者是千篇一律?据说是因为受到“文字狱”的影响。
这和“文字狱”的影响有什么关系?每个人总要开口说话。我们每个人,说话的时候,是不是个个都要“字斟句酌”?趋吉避凶,趋利避害!不知深浅利弊,趋避从何说起?
是!个中人,各自是会有一些取舍,言语间,也会有所选择。他们有可能是会把一些显戳的痕迹消弥于无形。那那些局外人呢?他们也深知利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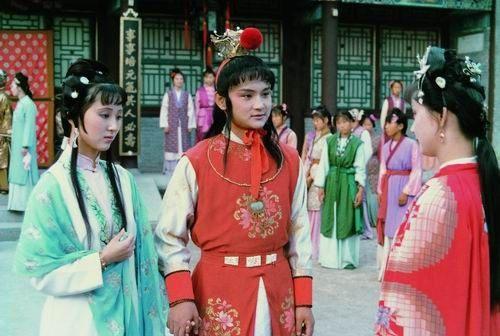
生活杂然无序,就象尧舜不能强巢许,巢许不能强尧舜一样,谁都不能例外。不管是你我他,还是你们我们他们,世法平等,是人人都一样,是个个都一样。清代的人和现在的人不一样?莫不是他们读了此书,就可以没有任何反应?为啥《红楼梦》在清代流行一百多年,读者留下的资料,仅仅就那么一点?
什么人之间,才会有共同语言?秦汉唐宋元明清,秦人和清人会有共同语言?《红楼梦》作者是哪一朝哪一代的人啊?清代的哪些作品和《红楼梦》是同一个时期的作品?
众人就连这点都说不清道不明的,那别的又从何说起啊?《红楼梦》,有说是和坤家事,有说是张勇家事,有说是明珠家事,有说是曹寅家事...

说到底,这都是清代的事。这些人,他们到底有没有经历过崇祯十七年的甲申之难,众人是不是都不大清楚?
朱由校在位七年,天启七年亦崇祯元年,天启二年尾,到崇祯七年初,不足十二年。天启二年到崇祯二年是七年,崇祯元年到崇祯七年,一样是七年。
天启16岁即位。在位7年,终年23岁,生有三男二女,均早年夭折,无一长大成人。天启二年,封由检为信王,五年后因无嗣,遗命由检继位,也就是崇祯皇帝。
由检继位,虽是兄终弟就,不殊由校命程延续,慈烺系由检之子,亦象由校之子。宝玉七岁实即崇祯七年,贾兰五岁,慈烺五岁!

天启二年到崇祯七年,也就十一年,虚闰两年,英莲十一,宝钗十三,宝钗英莲,实即天启的分身。——《红楼梦》里,英莲三岁,到宝玉出场七岁,实已经过七年一个月,两头算,已经是第九年。因宝钗生日在先,故英莲方满十一,宝钗已是十三。
再细考,雨村上京在八月,英莲四岁,六年三月以后,宝钗进了贾府,是十一月中,薛蟠十五岁,实则十四岁半。比宝钗大两岁,其实不足两岁,足足相差,也就是一岁八九个月。宝钗十三,同样不足十三。
朱由校(天启皇帝)1620年阴历九月到1627年阴历八月在位。
明熹宗于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十一日死后,由于没有子嗣,朱由检受遗命于同月丁巳日(二十四日)继承皇位,时年十八岁。第二年改年号为“崇祯”。——兄终弟就,间隔十三天。

崇祯帝即位后,即清除阉党,这个是在天启七年(1627年)十一月,崇祯帝铲除了魏阉羽翼——雨村判葫芦案,差不多也是在十一月左右。——这里,作者是把天启七年的事,移到崇祯七年了。
作者既要隐瞒事实真相,怎么可能原汁原味原样事实丝丝不乱叫人过眼即明?此所以作烟云模糊状的主因。但要与本事全不搭界,读者看朱成碧,必不能识辨其真。故其事虽乱,其实并不乱,其实作者自有一本帐目清如水明如镜萦萦在抱,殷殷记在心中。
若索要证据,这不是胡扯?但你解得作者的心锁,按序排序,对号入座非不能,未识其要,自不得其门而入。但,须得是一步不偏不倚,正中下怀。

我不敢说我自己的看法一些没错。但两府的末世,断不是清之末世。清造从顺治开始,顺康雍乾,如日方中,若言末世,便是欺人欺心欺天之论。天地人神三界,神鬼不容!方今世界,海晏河清,泾渭再不得分明,怪自己修行不到,没那个本事,谁阿在头上叫你不敢说真话不成?
旧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文字狱”离我们太遥远了,生在新世界,长在新社会,再不是作者所处年代,为什么不说实话?
清亡后,话三民,只说是前途无量,九一八,芦沟桥,又处水深火热!男儿血,补天裂,说英雄,唱英雄,国将亡,家难存,谁还顾得了《红楼梦》。这便是近世红学不得深入的原因。

掩卷沉思,往来如旧。六朝风物多如许,小照空悬壁上题。《红楼梦》曲,实影大明十六帝——崇祯以外的十五帝十四人(英宗两度临朝即钗黛合一),正册副册又副册,十四支曲,十四副判词,究其数。
但为十六帝各归各位,须熟悉十六帝迹!又得费时费力,我已不胜其力,惟我力所不及。我已疲惫,心力交瘁,大事要靠有大力者为。某实不胜其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