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高僧,愿承天下杀名,功过是非任凭后世说
大家-腾讯新闻2017-02-24 15:21
一、 庆寿寺双塔下的过路僧人 让我们从西长安街上一座消逝的寺庙说起吧。今天的长安街是近几十年发展起来的,两侧高楼林立,商业繁华,双向10车道现代化交通设施,气派、恢弘!而金、元至明至清至民国,这条大道(东单到西单)并未有很大变迁,其中一间800年的寺院及其两尊八角密檐砖塔,秀丽挺拔,卓尔不群,始终如一。
这两座塔分别建于蒙古国宪宗蒙哥汗七年(1257年)和宪宗蒙哥汗八年(1258年),是庆寿寺两位高僧——海云大师及其弟子可庵禅师的灵塔,而庆寿寺建于金章宗大定二十六年(1186年)。亦即是说,800年景物未动,添减些许,众生误以为时间也凝固不动。
换种说法,寺与塔巍峨800年,人间星辰转换,朝代更迭,阅历的便是那悲悲喜喜,你方唱罢我登场,不知是否也已厌倦之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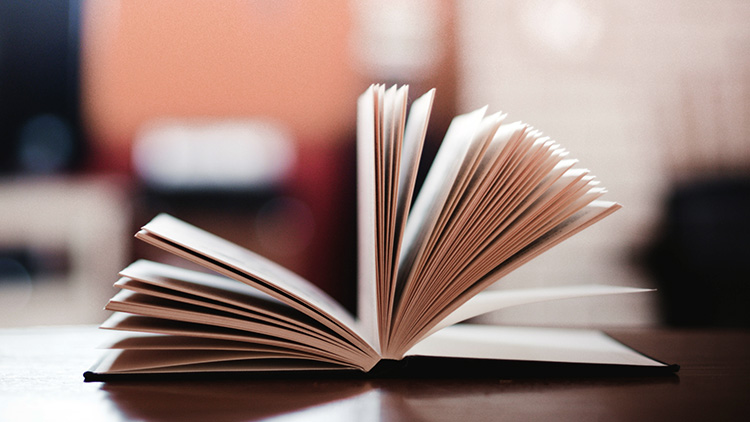
到了上世纪50年代中期,这寺院与灵塔终于到了寿终正寝的时刻。为了修建西单电报大楼及拓宽西长安街,主管北京市建设的某副市长下令拆掉它们,因为在建设规划上,寺与塔成了钉子户。这时梁思成又出来说话了,他提及“燕京十景”之一的“长安分塔”的弥足珍贵之处,情感与文学色彩俱佳。
所谓“长安分塔”,即是清晨时刻浪漫的光影投射,在太阳欲出时分,站在西单牌楼东南角——老长安戏院门外往东观瞧,就会看到庆寿寺两座塔一在路南,一在路北。走到近前再看,两座塔却都在路北的庆寿寺里面,挨得挺近,师徒俩灵塔,仿佛长幼相携。这光与影的错觉便是老城的神秘与浪漫。

梁思成建议至少保留双塔,即使它们在路中央,可以以环岛的方式辅以绿化,让双塔继续阅览人间至千年……但1955年已是梁思成陷入人生萎顿的开始,4月1日,林徽因去世。她以独有的倔强在指着鼻子指责前面那位副市长对文物的践踏之后,以很合宜的尊严离开一场对古城毁灭战。而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的梁思成则陷入那场所谓批判“两梁两胡唯心主义思想”(梁思成、梁漱溟、胡适、胡先准)的运动,他开始写检讨书……
梁思成的言论只是在几十年后的今天被人们津津乐道,他对庆寿寺的关怀只是美谈而已,他还保住了北海团城,但那种文人的无力感在当年不会引起更为重视的讨论。庆寿寺及双塔在1955年左右全部拆除,西长安街扩建,西单电报大楼的钟声为一个新时代敲响。
如果这个声音可以倒流往昔,它可否又惊着了另一位在此庆寿寺圆寂的高僧灵魂?那高僧便是姚广孝,住持庆寿寺20余年,只是庆寿寺过路僧而已,寺与他无关,塔更与他无关,他只是与大明朝奠定的厚重的开国基石相关。
二、 世上总有必然的相遇,注定的因缘无法错过 世上或许存在这样的人:他们应该相遇,为了历史的大事件而相遇,为了成就伟大的事业而相遇,相遇的焦灼感只在于:人生之短,那使他们相遇的因缘是否可以具足到来。
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8月朱元璋的正宫皇后——马皇后过世,朝廷召集分散于各地的有些声望的僧人们前往应天府(南京)皇宫为其超度法事诵经荐福。正是此次机缘,47岁的僧人姚广孝(时名“道衍”)初遇从北平奔丧过来的四皇子——燕王朱棣。两人一见如故,相谈投契。
9月,在奉天门,高祖朱元璋亲自为即将返回藩地的各位皇子挑选德行高尚的僧人,以陪伴他们回到自己的藩地,协助治理一方,固守边防,即所谓“阴翊王度”。这个决策与朱元璋早期曾经的出家经历有关,他希望治理领地也可以得到佛教的智慧裨益。他见到僧人道衍时,内心有惊异的触动,他恩准了四皇子朱棣将道衍分配给他带走的请求,并任命道衍住持北平庆寿寺。
朱棣与道衍注定没有辜负此生相逢,结下了“注定之缘”。彼时僧人道衍已47岁,在前一年已经接受了弟子供养的一根紫竹手杖,意味着进入长者行列,而22岁的朱棣如旭日朝阳,即将喷薄而出,他容颜俊朗,身形伟岸,文武双全,更重要的是已显示出一代大帝所应具备的坚强意志与自信。
在两年前他已经就藩燕地,多次受命参与北方边境抵御清剿蒙古人势力的军事活动,曾两次率师北征,招降元太尉乃儿不花,其军事才能是各大藩王之翘楚。
后人一直好奇这两位年龄相差25岁的君臣是如何一见如故,彼此吸引的。其实,从此后他们几近40年的君臣之谊可知,伴君如伴虎的臣子少有姚广孝这样始终与君王保持着平稳、平和且始终受到信赖的关系。他们一定是在这次结缘的初见上彼此看到了自己在对方身上映出的影子,而这正是他们内心中最为欣赏却并不会轻易示人的。再者,虎眼僧人道衍空有大志,到了人生的第47年终于等到这一天……
他们一去北平便是20年,等到朱棣再次以血腥屠杀的方式入主应天府南京的时候,已经是1402年,这20年中的17年他们在大明的北方边境,恪勤职守保卫国土。后三年便是掀起了强藩与中央王室的对抗,就是为争夺皇权发动的“靖难之役”。
作为一生笃持佛教的道衍和尚始终以高僧身份出入俗尘,为什么以最深入的最直接的甚至最凶狠的方式卷入这样一场残酷的屠戮杀生之役,长期以来为后世诟病,甚至有将其列入宗教参政的典型而直接损害到佛教的声誉。
“道衍”是法名,其幼时名天僖,字斯道,又字独闇,号独庵老人、逃虚子,长洲人(今苏州),医家出身,14岁出家至长州妙智庵。至今没有他俗家姓氏的记载。“姚广孝”是后期朱棣赐姓赐名。虽为佛弟子,但他交游广泛,好学不倦,精通儒释道、兵法医学甚至星象卜测。相士袁珙见过他后称其面相异于常人,三角眼犹如病虎,有嗜杀貌,类似元初佛家出身的名臣刘秉忠一般人物。(“是何异僧!目三角,形如病虎,性必嗜杀,刘秉忠流也。” ①)这次相面对道衍不知有否产生强烈的暗示作用,但他喜欢这样的称呼。

他唯一存世的画像收藏在紫禁城南熏阁里,名《姚广孝像轴》,确证了前述说法为真:虽说是他老年画像,但三角眼炯炯有神,目光澈亮,英武之气洋溢。在他赠袁珙的诗里这样写道:“岸帻风流闪电眸,相形何似相心优? 凌烟阁上丹青里,未必人人尽虎头。” ②此诗证实了袁珙相面之说。虎头燕颔专指王侯的贵相或武将威武之相。此诗表面自谦,说是那些供奉于名臣大夫的“凌烟阁”里,也未必都全是虎头燕颔之像,但实则颇为自赏。
燕王朱棣与建文帝朱允炆的彻底翻脸是一件大概率的历史必然事件,其祸根埋于明高祖朱元璋所作为。按理说,原来的嫡长子朱标立为太子继承王位没有任何问题,朱标本人品性温厚忠良,对兄弟关爱有加,包括朱棣在内没有不信服尊重这位兄长,朱元璋也是将其作为储君精心培养,但想不到的是天不假年,朱标竟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过世,给朱元璋沉重打击,这之后的几年基本是他悲伤恍惚,情绪混乱,不思理朝的垂暮之期。
他对朱标的钟爱使其没有正确的理性思考这个王朝平稳发展的问题,而是对孝顺善良的皇孙朱允炆爱屋及乌,将其立为皇太孙,直接继承帝位大统。他忘了那些在天寒地冻的遥远北方为其忠守江山的其他儿子们,此时他们都是拥有领地的藩王。按照朱元璋立下的祖训,藩王们不得任意返回帝京应天府(南京)。但祖训中开了一条例外,那就是一旦朝中出现奸臣,藩王们应该责无旁贷立马扬鞭疾驰而来杀灭乱臣,曰:“清君侧”。

点击此处,阅读原文
一、 庆寿寺双塔下的过路僧人 让我们从西长安街上一座消逝的寺庙说起吧。今天的长安街是近几十年发展起来的,两侧高楼林立,商业繁华,双向10车道现代化交通设施,气派、恢弘!而金、元至明至清至民国,这条大道(东单到西单)并未有很大变迁,其中一间800年的寺院及其两尊八角密檐砖塔,秀丽挺拔,卓尔不群,始终如一。
这两座塔分别建于蒙古国宪宗蒙哥汗七年(1257年)和宪宗蒙哥汗八年(1258年),是庆寿寺两位高僧——海云大师及其弟子可庵禅师的灵塔,而庆寿寺建于金章宗大定二十六年(1186年)。亦即是说,800年景物未动,添减些许,众生误以为时间也凝固不动。
换种说法,寺与塔巍峨800年,人间星辰转换,朝代更迭,阅历的便是那悲悲喜喜,你方唱罢我登场,不知是否也已厌倦之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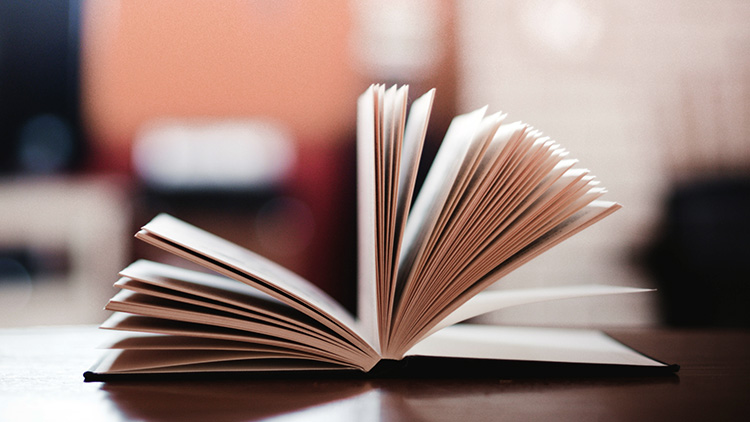
到了上世纪50年代中期,这寺院与灵塔终于到了寿终正寝的时刻。为了修建西单电报大楼及拓宽西长安街,主管北京市建设的某副市长下令拆掉它们,因为在建设规划上,寺与塔成了钉子户。这时梁思成又出来说话了,他提及“燕京十景”之一的“长安分塔”的弥足珍贵之处,情感与文学色彩俱佳。
所谓“长安分塔”,即是清晨时刻浪漫的光影投射,在太阳欲出时分,站在西单牌楼东南角——老长安戏院门外往东观瞧,就会看到庆寿寺两座塔一在路南,一在路北。走到近前再看,两座塔却都在路北的庆寿寺里面,挨得挺近,师徒俩灵塔,仿佛长幼相携。这光与影的错觉便是老城的神秘与浪漫。

梁思成建议至少保留双塔,即使它们在路中央,可以以环岛的方式辅以绿化,让双塔继续阅览人间至千年……但1955年已是梁思成陷入人生萎顿的开始,4月1日,林徽因去世。她以独有的倔强在指着鼻子指责前面那位副市长对文物的践踏之后,以很合宜的尊严离开一场对古城毁灭战。而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的梁思成则陷入那场所谓批判“两梁两胡唯心主义思想”(梁思成、梁漱溟、胡适、胡先准)的运动,他开始写检讨书……
梁思成的言论只是在几十年后的今天被人们津津乐道,他对庆寿寺的关怀只是美谈而已,他还保住了北海团城,但那种文人的无力感在当年不会引起更为重视的讨论。庆寿寺及双塔在1955年左右全部拆除,西长安街扩建,西单电报大楼的钟声为一个新时代敲响。
如果这个声音可以倒流往昔,它可否又惊着了另一位在此庆寿寺圆寂的高僧灵魂?那高僧便是姚广孝,住持庆寿寺20余年,只是庆寿寺过路僧而已,寺与他无关,塔更与他无关,他只是与大明朝奠定的厚重的开国基石相关。
二、 世上总有必然的相遇,注定的因缘无法错过 世上或许存在这样的人:他们应该相遇,为了历史的大事件而相遇,为了成就伟大的事业而相遇,相遇的焦灼感只在于:人生之短,那使他们相遇的因缘是否可以具足到来。
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8月朱元璋的正宫皇后——马皇后过世,朝廷召集分散于各地的有些声望的僧人们前往应天府(南京)皇宫为其超度法事诵经荐福。正是此次机缘,47岁的僧人姚广孝(时名“道衍”)初遇从北平奔丧过来的四皇子——燕王朱棣。两人一见如故,相谈投契。
9月,在奉天门,高祖朱元璋亲自为即将返回藩地的各位皇子挑选德行高尚的僧人,以陪伴他们回到自己的藩地,协助治理一方,固守边防,即所谓“阴翊王度”。这个决策与朱元璋早期曾经的出家经历有关,他希望治理领地也可以得到佛教的智慧裨益。他见到僧人道衍时,内心有惊异的触动,他恩准了四皇子朱棣将道衍分配给他带走的请求,并任命道衍住持北平庆寿寺。
朱棣与道衍注定没有辜负此生相逢,结下了“注定之缘”。彼时僧人道衍已47岁,在前一年已经接受了弟子供养的一根紫竹手杖,意味着进入长者行列,而22岁的朱棣如旭日朝阳,即将喷薄而出,他容颜俊朗,身形伟岸,文武双全,更重要的是已显示出一代大帝所应具备的坚强意志与自信。
在两年前他已经就藩燕地,多次受命参与北方边境抵御清剿蒙古人势力的军事活动,曾两次率师北征,招降元太尉乃儿不花,其军事才能是各大藩王之翘楚。
后人一直好奇这两位年龄相差25岁的君臣是如何一见如故,彼此吸引的。其实,从此后他们几近40年的君臣之谊可知,伴君如伴虎的臣子少有姚广孝这样始终与君王保持着平稳、平和且始终受到信赖的关系。他们一定是在这次结缘的初见上彼此看到了自己在对方身上映出的影子,而这正是他们内心中最为欣赏却并不会轻易示人的。再者,虎眼僧人道衍空有大志,到了人生的第47年终于等到这一天……
他们一去北平便是20年,等到朱棣再次以血腥屠杀的方式入主应天府南京的时候,已经是1402年,这20年中的17年他们在大明的北方边境,恪勤职守保卫国土。后三年便是掀起了强藩与中央王室的对抗,就是为争夺皇权发动的“靖难之役”。
作为一生笃持佛教的道衍和尚始终以高僧身份出入俗尘,为什么以最深入的最直接的甚至最凶狠的方式卷入这样一场残酷的屠戮杀生之役,长期以来为后世诟病,甚至有将其列入宗教参政的典型而直接损害到佛教的声誉。
“道衍”是法名,其幼时名天僖,字斯道,又字独闇,号独庵老人、逃虚子,长洲人(今苏州),医家出身,14岁出家至长州妙智庵。至今没有他俗家姓氏的记载。“姚广孝”是后期朱棣赐姓赐名。虽为佛弟子,但他交游广泛,好学不倦,精通儒释道、兵法医学甚至星象卜测。相士袁珙见过他后称其面相异于常人,三角眼犹如病虎,有嗜杀貌,类似元初佛家出身的名臣刘秉忠一般人物。(“是何异僧!目三角,形如病虎,性必嗜杀,刘秉忠流也。” ①)这次相面对道衍不知有否产生强烈的暗示作用,但他喜欢这样的称呼。

他唯一存世的画像收藏在紫禁城南熏阁里,名《姚广孝像轴》,确证了前述说法为真:虽说是他老年画像,但三角眼炯炯有神,目光澈亮,英武之气洋溢。在他赠袁珙的诗里这样写道:“岸帻风流闪电眸,相形何似相心优? 凌烟阁上丹青里,未必人人尽虎头。” ②此诗证实了袁珙相面之说。虎头燕颔专指王侯的贵相或武将威武之相。此诗表面自谦,说是那些供奉于名臣大夫的“凌烟阁”里,也未必都全是虎头燕颔之像,但实则颇为自赏。
燕王朱棣与建文帝朱允炆的彻底翻脸是一件大概率的历史必然事件,其祸根埋于明高祖朱元璋所作为。按理说,原来的嫡长子朱标立为太子继承王位没有任何问题,朱标本人品性温厚忠良,对兄弟关爱有加,包括朱棣在内没有不信服尊重这位兄长,朱元璋也是将其作为储君精心培养,但想不到的是天不假年,朱标竟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过世,给朱元璋沉重打击,这之后的几年基本是他悲伤恍惚,情绪混乱,不思理朝的垂暮之期。
他对朱标的钟爱使其没有正确的理性思考这个王朝平稳发展的问题,而是对孝顺善良的皇孙朱允炆爱屋及乌,将其立为皇太孙,直接继承帝位大统。他忘了那些在天寒地冻的遥远北方为其忠守江山的其他儿子们,此时他们都是拥有领地的藩王。按照朱元璋立下的祖训,藩王们不得任意返回帝京应天府(南京)。但祖训中开了一条例外,那就是一旦朝中出现奸臣,藩王们应该责无旁贷立马扬鞭疾驰而来杀灭乱臣,曰:“清君侧”。

点击此处,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