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翔|文学如何“破圈”
2021-11-19 12:16阅读:
饶翔|文学如何“破圈”
饶翔,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供职于光明日报文艺部,担任“光明文化周末”副主编。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艺评论中心特邀研究员。在各类报刊发表文学评论文章二十余万字,有多篇被转载或收入中国大陆及港台地区选本。出版文学评论集《重回文学本身》《知人论世与自我抒情》。曾获“中国新闻奖”一等奖、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奖、百花文艺奖等。《重回文学本身》入围2014年度“花地文学奖”文学批评奖;《知人论世与自我抒情》获2017年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优秀作品。
 长江文艺 文学新批评
前天
长江文艺 文学新批评
前天

饶翔|文学如何“破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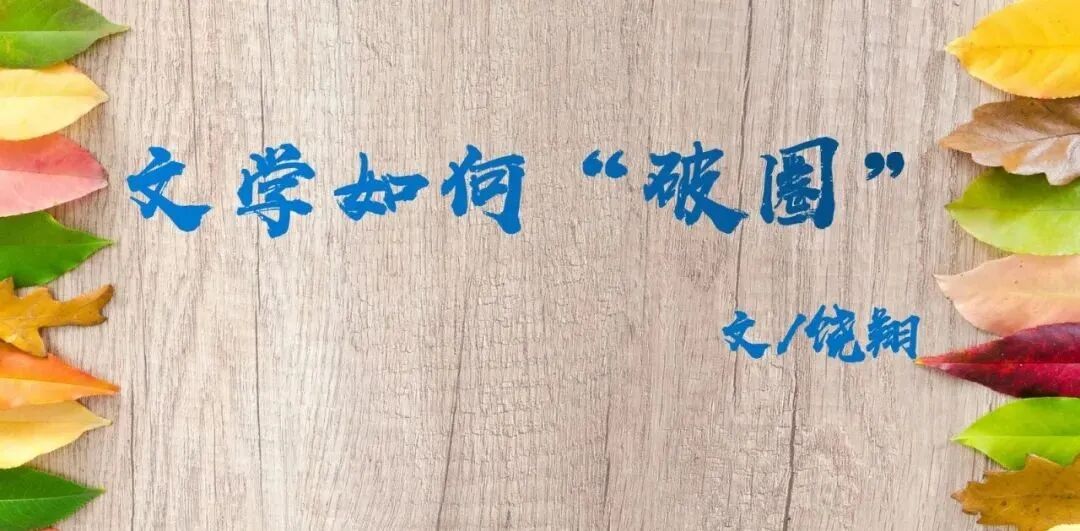
“
编者按
“跨界”“破圈”是时下文化场域十分热门的词汇,文学领域同样如此。这种现象背后隐含着文学从业者对于文学日渐边缘化的现状的不满,以及试图打破现状、突破困境的期待和努力。讨论如何打破文学边界、实现“破圈”生长,不仅要培植一种意识、凝聚一种期待,更应细究其内在逻辑,找到切实可行的路径。今日分享饶翔《文学如何“破圈”》,在本文中作者以脱口秀节目的热播为切入点,立足近年来文学的现实,探究“文学”破圈的根本动力,以及“破圈”对作家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本文原发《长江文艺》2021年第11期,感谢《长江文艺》授权转载。
 ROCK&ROAST
ROCK&ROAST

 S4
S4

2020年夏天,脱口秀大会第三季带给人们的感动与快乐还未远去,第四季又如期来临。尽管本季脱口秀大会的外界反响和受关注度明显不如上一季,但凭借着上一季屡屡冲上热搜的话题热度,脱口秀这种文化娱乐形式已经成功“出圈”,在大众层面尤其是年轻观众群体获得了广泛影响。在去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紧张焦虑、忐忑不安的氛围中,脱口秀在某种程度上抚慰了很多人。我要承认,那段时间,我反复刷着某些精彩片段,津津有味,乐此不疲,我也跟身边的小伙伴们多次讨论过各自钟意的选手、喜欢的段子。后来便有了在北京师范大学的一次小型的讨论会。在受邀主持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青年文学与青年文化工作坊”的第一期活动时,我与工作坊的组织者本来商定就专门讨论脱口秀,因为这无疑是当前颇具影响力的一种青年文化形式,后来由于要兼顾对青年文学创作的讨论,于是便将主题拓展为“我们如何‘破圈’——当代青年文学与文化生活”。
所谓“破圈”本是网络流行语,由“出圈”演化而来,指某个人或他的作品突破某一个小的圈子,被更多的人接纳并认可。自然,
在一个“内卷化”时代,如何能“破圈”,绝不只是哪一个圈子的焦虑,而提出“我们如何‘破圈’”,确实包含着我们这些文学从业者对于当前文学状况的不满与困惑。一方面,传统严肃文学不仅早已失去轰动效应,甚至还失去了基本的读者,其社会功能在不断弱化,“熏浸刺提”“支配人道”的“不可思议之力”或消散,或转移;而另一方面,文学的圈子化问题日益突出,主流文学界似乎颇为流连圈子内部的风景,很是享受圈子内的舒适与安稳,岁月一时静好。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也得益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但凡有些名气的作家生活得还很不错——这本是好事,然而,他们是否还有“破圈”的动力呢?

很长一段时期以来,中国文学陷入了一种近乎无解的内循环:随着上世纪末,“文学失去轰动效应”,大众文化迅速兴起,传统严肃文学逐渐边缘化,读者日益稀少,使作家从大众领域退回到了文学领域;而文学囿于一圈之内,又使读者进一步地减少,圈子化问题日益严重。一些广为诟病的现象或许也跟圈子化密切相关,诸如文学批评的问题——文学如果只是圈子内部少数人的游戏,一个作家的作品如果再没有读者的竞相传阅、奔走相告作为辛苦创作的甜蜜回报,那么评论家为何还要吝惜自己的赞美呢——纵使言过其实,那也是出于对同行的善意的慰藉。或者说得再悲情一点,那不也是寒意萧瑟中寂寞者之间的抱团取暖吗?在此情况下,文学批评如果不进入学院系统成为文学研究,那么,它的主体性又如何确保呢?
诚然,大的文化环境发生了可谓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这个被“五四”先贤们宣告“已经过去了”的陈腐价值,又魂兮归来,与“言志”“载道”等“高大上”的文学传统一起,面无愧色地宣告自身的合法性;尤其是以欲望作为驱动机制的网络文学不仅迅速占领市场,收割读者,而且毫不掩饰想进一步登堂入室“主流化”的野心。如果说网络文学的风靡还颇具“中国特色”的话,那么,大众消费文化一统江湖,则刷新了西方学者对于人类的认知:“我们终于承认人类的生存与真理、理性有关,但至少与幻想、欲望有关”,“学问不再是象牙塔之事……它们回归到日常生活”
[1]。于是文化研究兴起,文化理论盛行。在欧美大学校园里,传统的文学课程已经大量被传媒研究、人类学、新历史学、政治学、女性研究等被统称为“文化研究”的这门超级学科所取代。在国内,文化研究也风靡一时成为显学。

在某些乐观的学者看来,尽管“文学”作为一个艺术门类,或是作为一门强大学科的存在遭遇了巨大的危机,然而,文学的“幽灵”正在其他文化类型中显现,不论是电影、电视、新闻报道,还是商业广告、娱乐节目,甚至是在高度“仿真化”的日常生活中,文学的“幽灵”无孔不入,文学性的思维和语言文本无处不在,想象的逻辑似乎已经不战而胜,被消费的、娱乐的、数码的,乃至存在的规则暗中接纳。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早就“出圈”了,我们要做的是欢呼迎接一个“大文学”时代的来临。
[2]这样的看法自然不无道理,我们在脱口秀中就能得以印证——一段精彩的脱口秀表演中少不了形象、叙事、修辞等语言艺术的加持,甚至脱口秀大会的策划者李诞本身就是一名重度文学青年,使人不由猜想他是否将其未能发挥尽兴的文学才华投注到了脱口秀这种形式当中?更有意思的是,在爆得大名之后,李诞却依然怀抱着纯文学的理想,出版了一本“比纯文学还纯”的中篇小说《候场》,甚至还加入了上海市作家协会。而依靠脱口秀大会成功“出圈”的网红李雪琴,则在访谈中自曝当年考入北大时最想上的并非新闻传播学院,而是中文系,尽管最终学了广告学,但在投身短视频创作及至脱口秀节目后,她依然需要依靠不断的文学阅读来获得创作的灵感。这或许也正印证了某些学者的看法,尽管中文系不断地被传播学院、媒体系之类的新学科瓜分,但后者不过是中文系换汤不换药的别名而已,至少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文学学科的主要课程依然是这些新学科的基础课程。而那些在平面媒体或视觉媒体大展宏图的新一代文化精英,都逃不脱被中文系训练的命运。
[3]
“


2
021年7月,“小说革命”与无界文学活动在西安举行,“无界·收获APP双盲命题写作大赛”启动仪式同期举行。
尽管如此,尽管“诗意”或者说“文学性”似乎弥漫在当前所有的文化活动中,但我们依然需要追问的是,“一首诗究竟在哪儿?”[4]——严肃文学的本体性究竟在哪里(如果有的话)?位置在哪里、边界又在哪里?前不久,在一场名为“‘小说革命’与无边界文学”的活动中,中国作协副主席、评论家李敬泽指出,就所谓“小说革命”以及“无边界”、跨文体的写作而言,
“在文体或者说文类上做种种跨越的花样,并不能解决多大问题。根本的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我们拓展甚至发明新的文学性,需要我们开拓新的边界,走到更为广阔的原野上去”。李敬泽在此所说的“文学性”,已经不是指那能够附着在任何文化形式上的“幽灵”,而是指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的最本质属性,它既是形式,也是内容。
李敬泽关于“发明新的文学性”的观点,让人联想到德勒兹关于“生成文学”的论述。德勒兹所说的“生成”是一个“辖域”和“解辖域”的交替过程。辖域是建立了自己的领土和法则的强势性存在,阻碍和束缚了进一步的生成。而生成最大的任务就是创造,通过创造来突破各种编码方式,通过创造出新的、尚未出现的存在来呼唤新的力量加入现有的力场,从而改变各种限制和束缚的强势存在,这便是解辖域。德勒兹认为,文学是生成的通道之一,它通过运用语言材料,利用文学虚拟的力量创造全新的存在,在生活和权力的内部产生一个全新的、需要重新审视的存在,就像在一个既存的力场中加入一个全新的力,瞬间改变了整个力场的格局,让力场处于动荡和摇摆之中,这就是生成文学的力量和作用。
[5]或许我们可以将圈子化和“破圈”之间类比成一个辖域和解辖域的动态关系,而新的文学性的生成,也正有赖于我们以“破圈”来挣脱圈子化的强势限制与束缚。按照德勒兹的看法,解辖域之后又会“再辖域化”,而“破”与“立”之间不断循环往复也是这个领域有活力的表征。
严肃文学“破圈”的另一重动力则源于对其社会功能与影响力的焦虑:如何重新成为一支活跃的、有效的文化力量,甚而至于,能重获文化领导权。作家们的“破圈”意味着,他要走出他容易沉湎其中的幽微狭小的情感世界,走出那些写作的“舒适区”,“关心粮食和蔬菜”,深入日新月异的社会生活,“走到更为广阔的原野上去”。我由此回想起曾参加过的一个金融小说的作品研讨会,当座上不止一位评论家表示不熟悉作者所书写的中国当代金融资本世界,同时却以一套传统“纯文学”标准对作品指手画脚时,使人感到那是怎样的一种傲慢与偏见,而文学又是如何画圈自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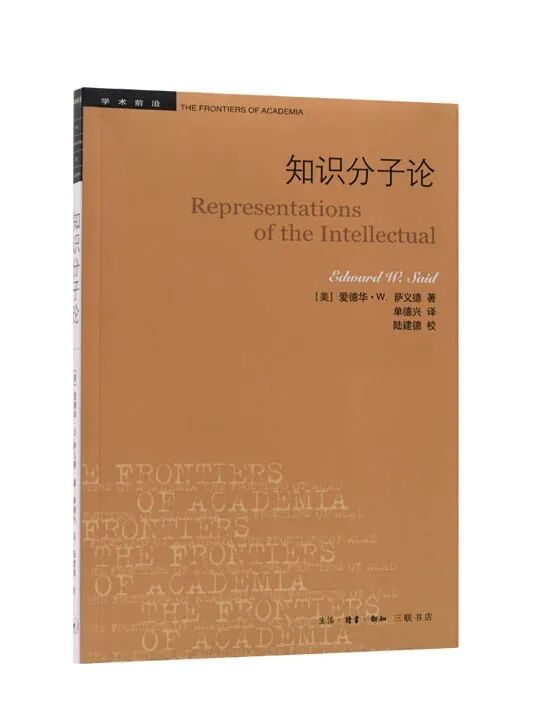
作家“破圈”意味着他要努力成为具有公共性的知识分子。在《知识分子论》中,萨义德认为,葛兰西把知识分子视为符合社会中一套特殊作用的人,
这种社会分析远较精英俯瞰的观点接近现实,尤其在20世纪末,许多新兴行业印证了葛兰西的见识——广播员、学院专业人士、电脑分析师、体育运动和媒体律师、业务顾问、政策专家、政府顾问、特殊市场报告的作者,以及近代大众新闻业这一行本身,知识分子的衍生扩大到了许多领域。但是萨义德也提示了其中存在的危险:“知识分子的风姿或形象可能消失于一大堆细枝末节中,
而沦为只是社会潮流中的另一个专业人士或人物。”圈层化导致知识分子可能广泛地被收编。因此,萨义德赞赏知识分子的行动能力,“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
( to)’公众以及 ‘为 ( for) ’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与葛兰西一样,
萨义德强调知识分子的“代表 ”职能。“知识分子是以代表艺术为业的个人,不管那是演说、写作、教学或上电视。”事实上,
萨义德的这本《知识分子论》正是他在英国广播公司 ( BBC)所做的系列演讲的结集。当传媒成为当代文化生产和传播最主要的形式时,
如何利用传媒向公众发言,
以期影响整个文化形成,是知识分子要积极面对的问题。一方面,需要抗拒、防止由权力和资本运作所造成的媒体的见解和才智的“刻板印象”,“知识分子只有借着驳斥这些形象……借着提供米尔斯所谓的揭穿或另类版本,竭尽一己之力尝试诉说真话,才能加以抵抗。”另一方面,
知识分子要拥有高超的代表“艺术”,“这包含了福柯所谓的‘不屈不挠的博学’,搜索另类的材料, 发觉埋藏的文件,
唤回已被遗忘(或放弃)的各类历史。这包含了一种戏剧感和起义感,善用一己罕有的发言机会,博取观者的注意,
比对手更具有才智、更善于辩论。”
[6]文学要“破圈”也意味着对作为知识分子的作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便是能突破文学专业性的壁垒,具有处理公共议题的能力,具有吸引公众的魅力以及善于面向公众发言的才能与艺术。自然,在大众传媒时代,在情绪易于压倒事实的所谓“后真相”时代,如何避免以夸张片面之词迎和媚俗、哗众取宠,也是严肃的作家们需要警醒之事。
 注释:
注释:
[1] [英]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商正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
[2] 陈晓明:《文学的消失或幽灵化?》,收入《不死的纯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 同上。
[4] 姜涛:《一首诗又究竟在哪儿——陈东东·全装修·解读》,《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2期。
[5] 葛跃:《德勒兹生成文学思想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
[6] [美]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三联书店2002年版。
文字|《长江文艺》2021年第11期
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