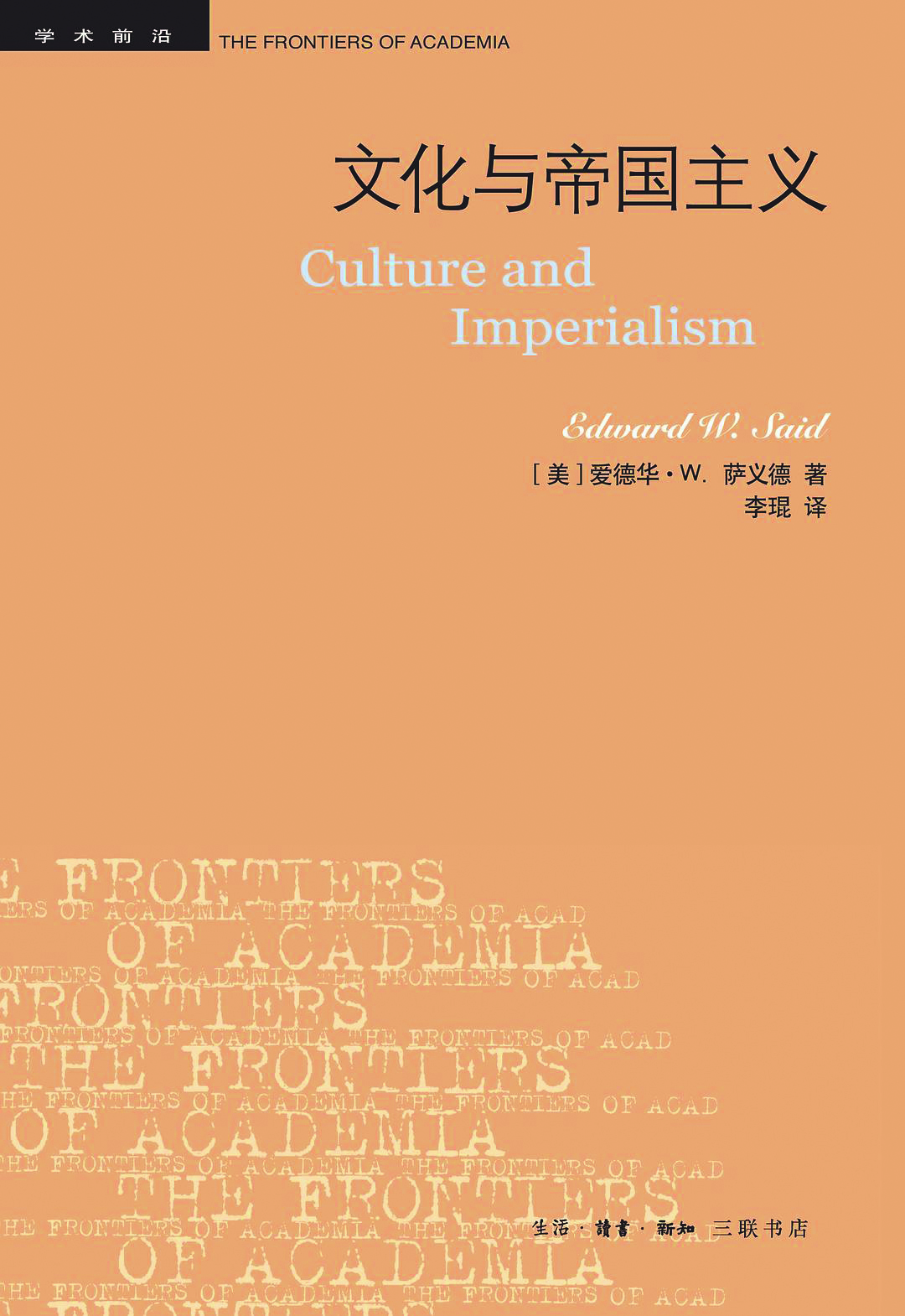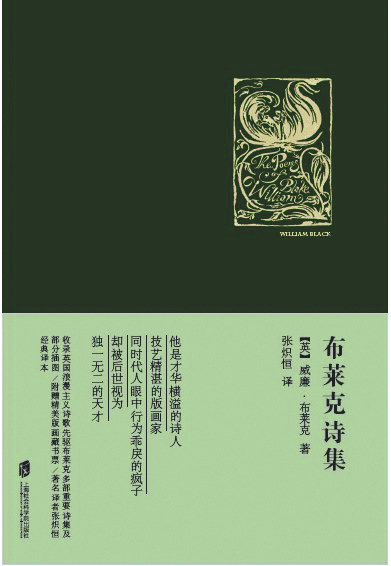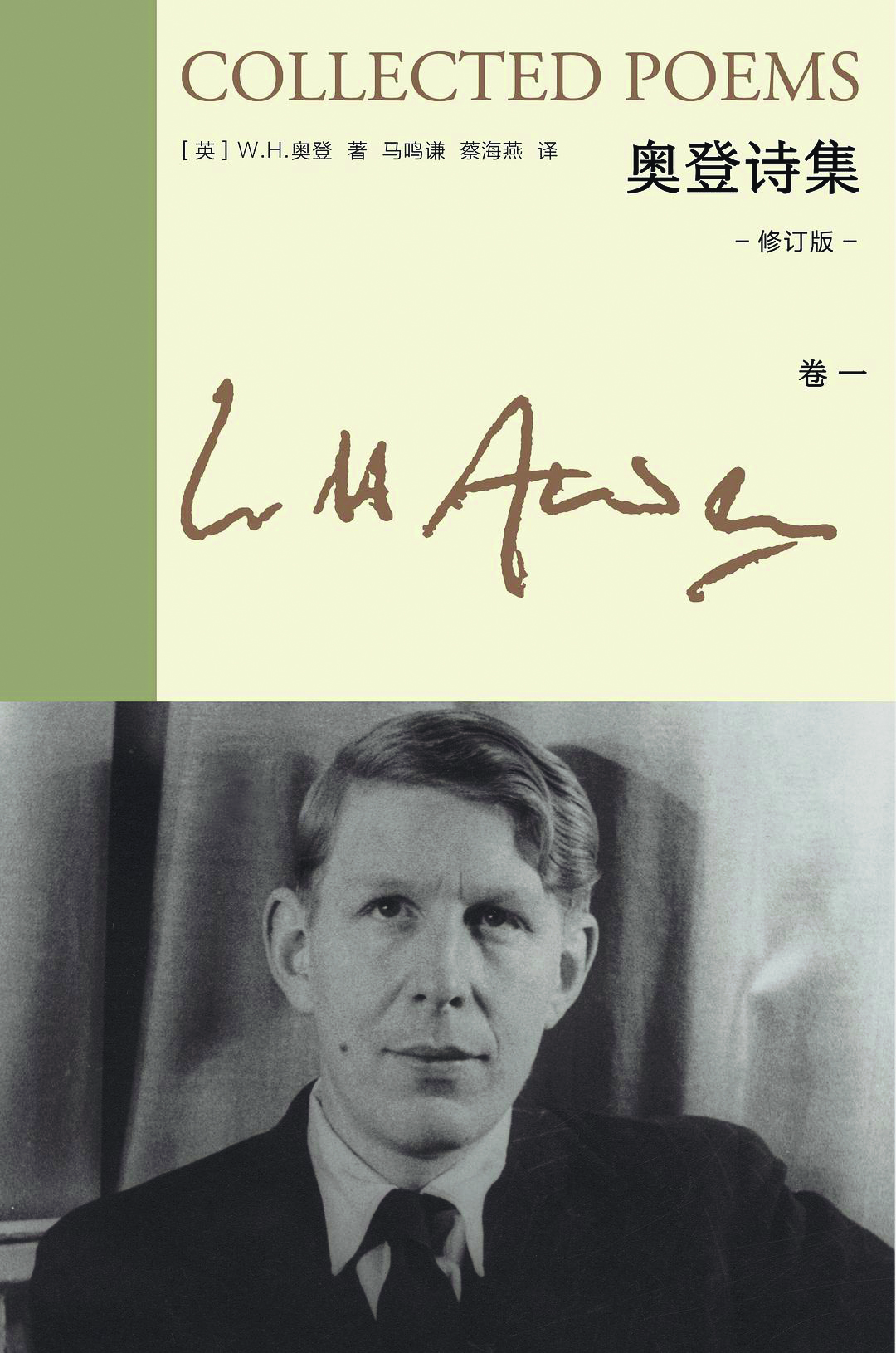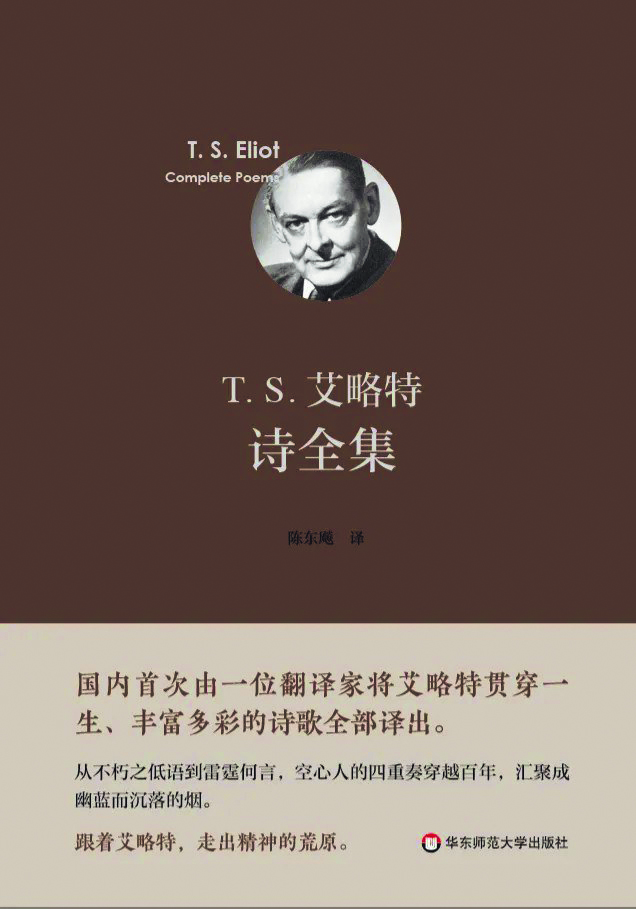新浪博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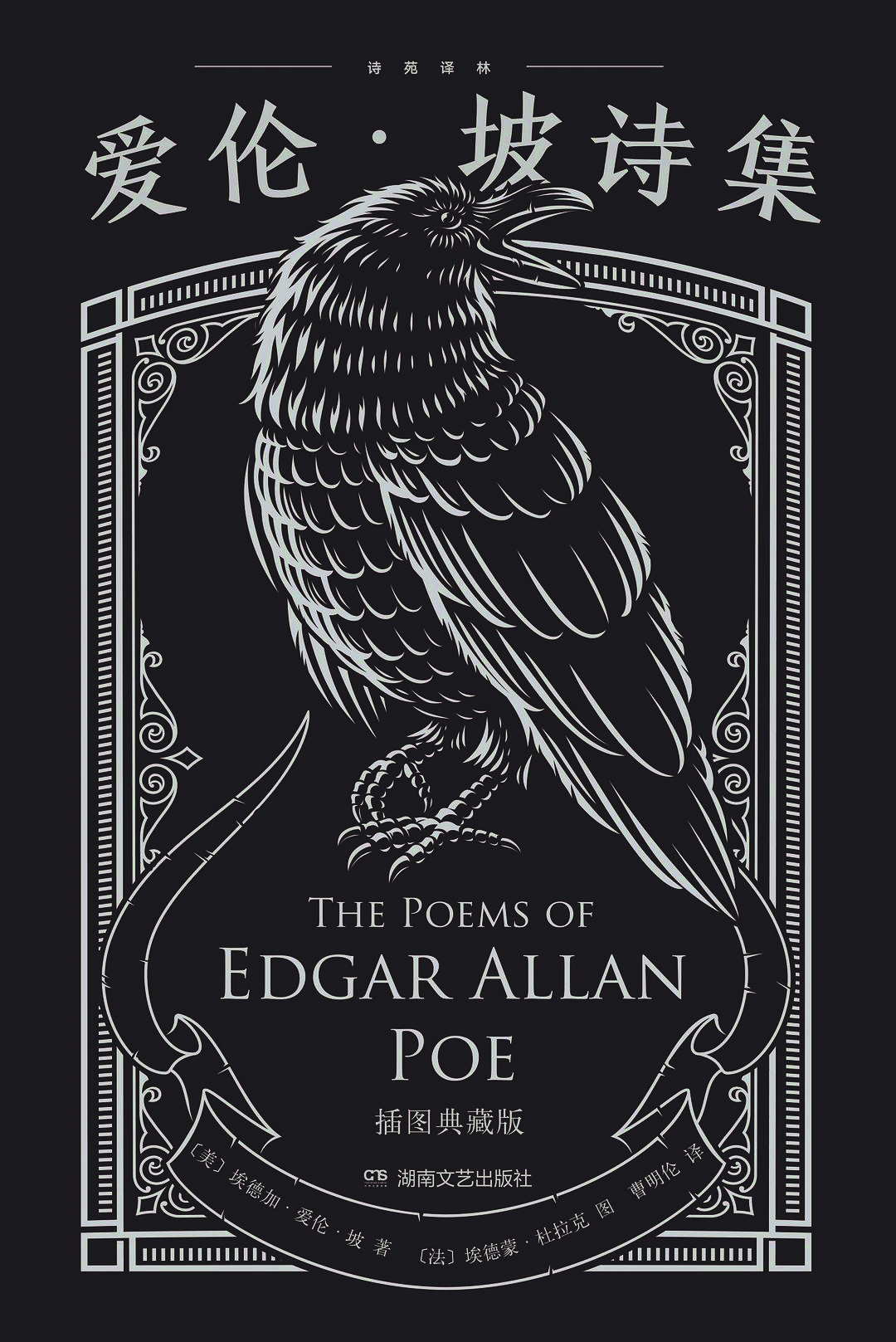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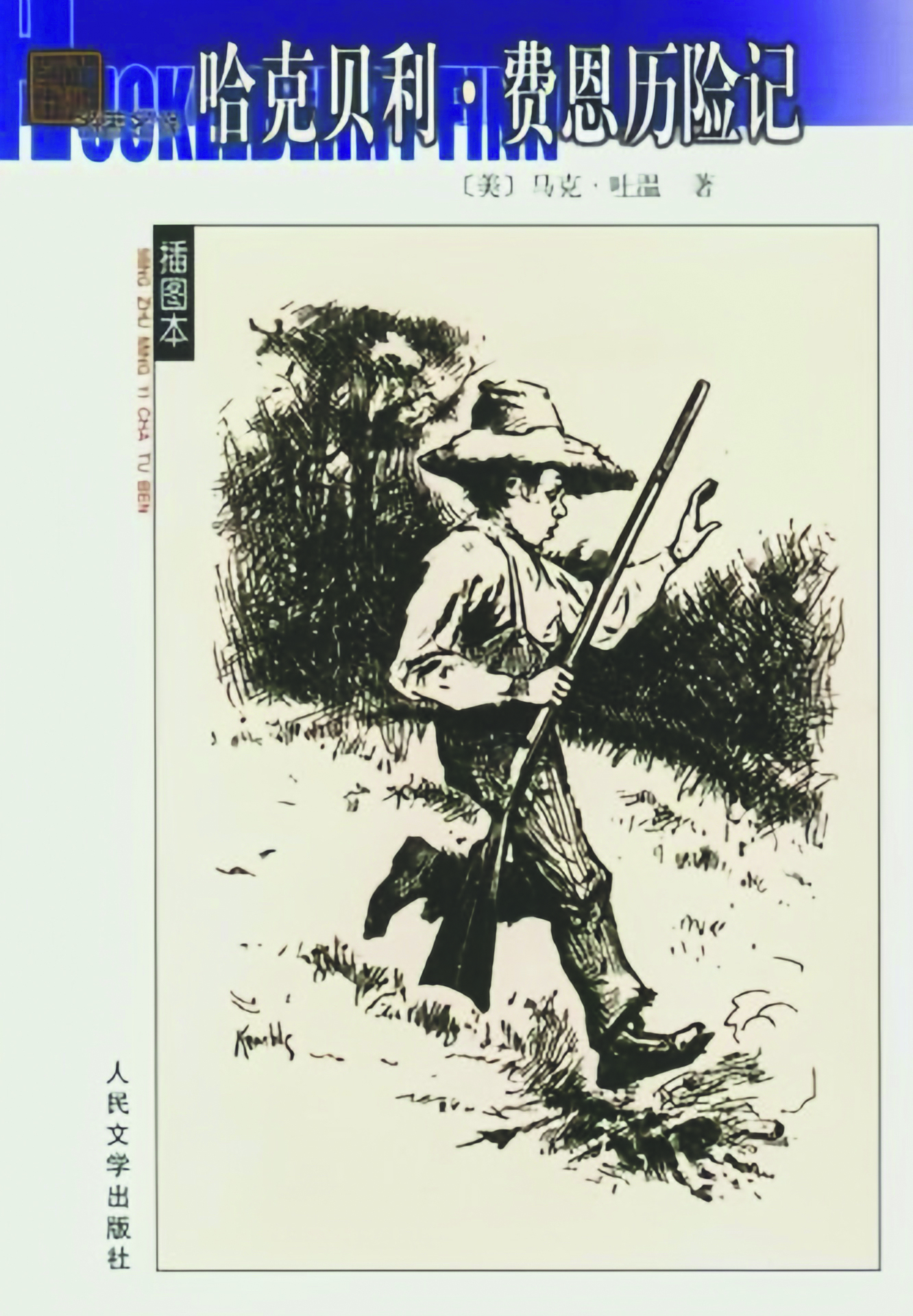

大江健三郎 部分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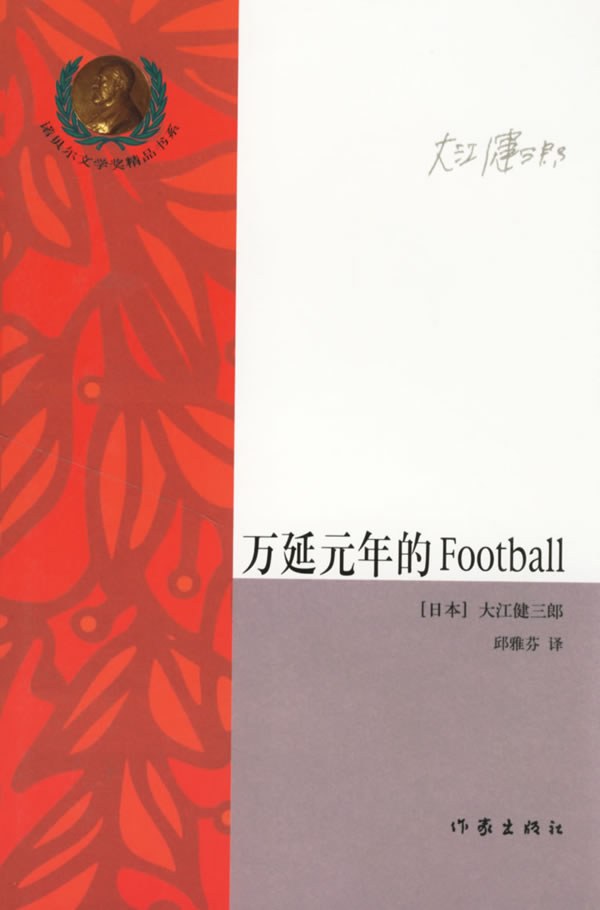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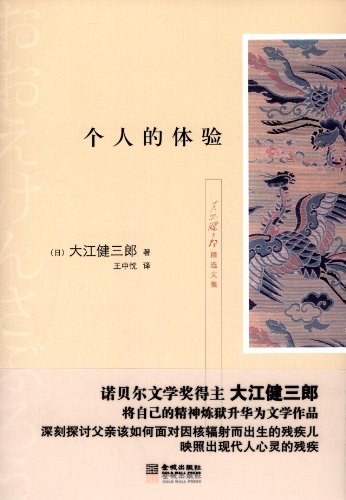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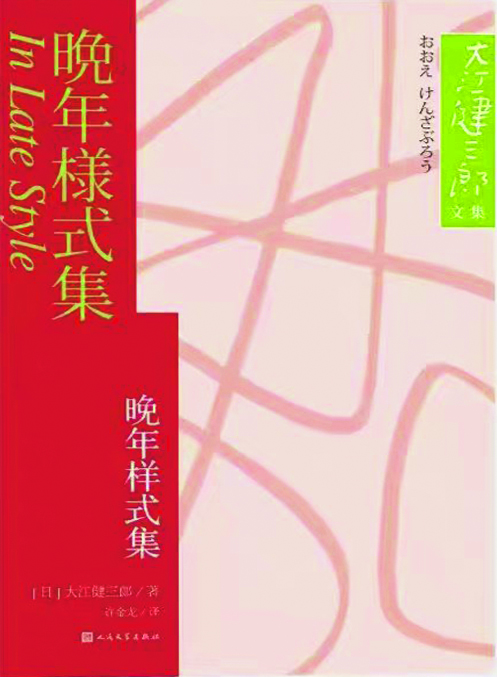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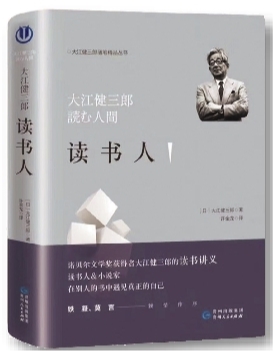
《读书人》,【日】大江健三郎著,明迪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19年3月

大江健三郎
《读书人》于2007年由日本集英社出版,作者大江健三郎时年72岁。作家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也先后于2011年、2019年出版了许金龙翻译的中译本。大江在《读书人》中,诚挚地讲述了其“读书人”生涯,说他书房中的书与他血脉相连,指出其读书特点是一种持续性阅读,而其最重要的生活特点就是“与书为伴”。他在《读书人》中文版自序中说:“该书不仅仅是‘读书讲义’,它还最为真实和详尽地讲述了当下的我本人是如何生活过来的,所期盼者为何物。”
《读书人》由大江系列讲座整理而成,具有口述体自传的性质。全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生活·读书”是该书的主干部分,第二部分“‘晚期风格’之思想——全面阅读萨义德”专门讲述作家的萨义德阅读体验,整部书展现了生活、读书、创作三位一体的大江的人生历程。可以说,这是一个作家的生命历程,也是一个同时代读书人、知识分子的生命历程。
早期阅读与创作生涯的开始
少年大江就爱上了阅读。对于生活在偏僻村落里的当时的孩子而言,书籍是一种奢侈品。从9岁至13岁这五年间,大江只能反复阅读一本书——马克·吐温的小说《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这本书令少年大江深深地感受到了故事的魅力和语言的力量,大江终其一生的阅读兴趣由此生发。此后,从高中至大学时代,大江又先后邂逅了其人生中的四本重要书籍。
第一本是时任东京大学法国文学教授渡边一夫的《法国文艺复兴断章》。当时正值“二战”后不久,对于刚刚升入高中的大江而言,书中“唯有人文主义,才能够拯救人们”等话语触动了他。他了解到渡边一夫是东京大学法国文学教授,便决定考入东京的大学,以便有机会亲炙渡边一夫,大江直言这是决定其人生轨迹的一本书。
第二本是《爱伦·坡诗集》,尤其其中《安娜贝尔·李》的日文译文令高中二年级时的大江赞叹不已,文字的力量再次震撼了大江,他说:“我开始对文学语言充满惊异,这种感觉因为这本《爱伦·坡诗集》而萌醒了。”大江还发现了将英文原诗与日文译诗进行对照阅读的乐趣,由此获得了一种对文体的感受力。《安娜贝尔·李》成为一种近乎恒久的诗意想象,大江将这种诗意想象融入了2007年出版的晚期代表作之一《优美的安娜贝尔·李 寒彻颤栗早逝去》中。
第三本是大江在大一时邂逅的题名为《艾略特》的诗集,译者是日本英国文学研究者深濑基宽。《艾略特》中的英文原诗与日文译诗印在同一页上,令喜欢对照阅读的大江感到了一种持久的阅读魅力,他对《J·阿尔弗瑞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的译文更是赞叹不已,再次折服于语言的魅力。于是,他用大约半年时间持续地阅读这本诗集,这种慢读方式是大江重要的文学修炼方式之一。
第四本是大江在大二时邂逅的《奥登诗集》,也是深濑基宽翻译版,这本诗集的编排形式是将英文原诗附在诗集末尾。大江在阅读这本《奥登诗集》的过程中,感到他所憧憬的现代文体清晰地显现出来了,“在奥登题为《一九二九年》的诗歌里发现了非常优美的文体,这种文体能够更为确切地表现出现代社会中的事物。”
通过上述作品,大江不断地思考着文章的表述方式,同时也思考着“人”的状态问题。经过这种持续的阅读和思考,大约两年后,大江在1957年5月22日的《东京大学新闻》上发表了《奇妙的工作》,受到著名评论家平野谦的关注,《文学界》《新潮》《近代文学》等日本著名文艺杂志开始接连邀请他发表作品,大江长达六十余年的创作生涯由此扬帆起航。这是阅读的力量,同时也是思考的力量。
敏锐的文体意识
大江文体似乎是一个说不完、道不尽的话题,有人诟病其浓郁的翻译味,有人赞赏他将新语导入了日语世界。大江于199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万延元年的Football》是其获奖代表作之一,大江在作品开篇部分使用“咽下”“内脏”等硬质汉语词汇,导入“钝痛”“沉重肉体”等诗歌意象,将安保斗争失败后的至暗时刻形容为“黎明前的黑暗”,并将“黑暗”中的无根、徒劳感表达得淋漓尽致,提示了一种全新的日语表达方式,内含引发语言革命的冲击力。音乐家武满彻赞扬大江的语言具有无与伦比的质感,且这种质感源自作家凝视内面世界时的清澈目光。松原新一也认为开篇部分内含绝妙的诗性隐喻,象征着小说主题的诗意表述。可以说,大江文学的语言、文体、思想三者密切相连,形成三位一体的相生或相克关系。
大江入读东京大学法国文学专业后,热衷于将法语文本与日语译文进行对照阅读,这不仅有助于法语学习,也深化着他对小说语言的认知。大三那年,大江终于写出了短篇小说《奇妙的工作》。平野谦评价“作为短篇形式的完成度很高,还发现其内容亦富于新意。”
大江具有敏锐的文体意识,自言并非天生拥有出色文体者,而是在阅读中不断思考、不断创新。渡边一夫高度赞赏大江的这种阅读抑或创作人生,他在大江临近毕业之际,指导大江每三年选择一个新的阅读对象,然后集中阅读其作品。大江长期恪守渡边一夫的教诲,每隔三年便开启新的阅读模式,与阅读对象进行着穿越时空的神游,并不断地思考、创造着新的大江文体。
经典文学的滋养与抚慰
卡尔维诺说:“经典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经典的重读价值在于其深厚的精神底蕴和持久的价值魅力,它可以穿越时空,滋养灵魂,使生命升华。大江在其文学起步阶段,曾经长期痴迷于诗语之美,在小说占据文学中心舞台的时代,这也是一种与经典对话的方式。事实上,大江一生与书为伴,当他感到痛苦时,也会通过读书排忧解烦。从《读书人》中列举的书目看,大江无疑是一位经典阅读者。
青年大江曾经风光无限,1958年以短篇小说《饲育》获得日本纯文学大奖芥川奖,由此成为炙手可热的日本文坛新人,当时他还是一名大学在校生。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63年出生的长子大江光患有先天性脑瘫,大江的人生遭遇了沉重的一击,他最终选择了与残疾儿共生之路,《个人的体验》等作品即以此人生体验为素材创作而成。大江光长到十四、十五岁时,开始遭遇严重的青春期烦恼,大江知道儿子“遇上了此前不曾经历的痛苦”,他从儿子的目光中读出了与威廉·布莱克诗歌中“悲叹”一词相近的情感,因而“理解了孩子的悲伤,理解了与此相接相连的自己的悲伤。”
这时,大江的脑海中浮现出威廉·布莱克的《小男孩的迷失》《小男孩的寻获》《别人的痛楚》等诗歌。威廉·布莱克在《别人的痛楚》中写道:“我能看着别人哀愁/而不觉得心里也难受?”“父亲能看着孩子哭泣/而不觉得满心戚戚?”“母亲能坐着倾听/幼儿发出恐惧的呻吟?/不,不,永远不会,/永远,永远不会。”这些诗句带着浓郁的哀伤气质,大江从中还发现了诗语之美,并以《别人的痛楚》为例,指出该诗在展现布莱克根本精神的同时,还是柔美诗歌的典范。这些柔美的诗句带来强大的精神力量,大江说他在那段时期一直通过阅读布莱克的作品而获得支撑,他还将这时期的情感体验写成了《新人呀,觉醒吧!》,这是经典的力量。
大江在50岁前后似乎遭遇了中年危机,对其漫长的创作生涯产生了怀疑。当然,大江再次通过阅读超越了危机,从48岁至50岁的三年间,大江专心致志地阅读了但丁的《神曲》,还大量阅读了相关研究著作。这次阅读为大江带来崭新的体验,认为但丁表现了这个世界的“至上之物”。他高度评价约翰·罗斯金的但丁观,将但丁想象力的核心定义为对终极真理的追寻。这是大江对经典价值的发现,经典为其内心带来了明晰的坐标。大江以这三年的阅读经验为基础创作了《致令人眷念之年的书信》。就这样,大江不断地从经典中汲取着力量,他在《读书人》中写道:“所谓经典,就这样以各种形式一次次地为我们唤起全新的、深层的感受。尤其是步入老年之后,经典将会赋予我们丰富的经验。”
走进萨义德
《读书人》第二部分“‘晚期风格’之思想——全面阅读萨义德”主要以大江阅读萨义德的最后著作《论晚期风格:格格不入的音乐与文学》体验为中心展开。1990年,55岁的大江第一次与萨义德交谈,那是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校区举办的一次学会上,此后二人一直保持着通信关系。2003年,萨义德去世后,大江重新阅读了萨义德的全部著作,还为萨义德的最后一本著作《论晚期风格:格格不入的音乐与文学》写了推介文。“晚期风格”是基于对生命之流、时间之流的感悟,是对“超越时间的时间”的深邃想象。大江说他一面品味着愉悦,一面长期持续地阅读着这本书,因为他也在思考他的“晚期风格”,希望再写一部“晚期作品”。通过这种持续的阅读与思考,大江创作了《晚年样式集》,2013年由日本讲谈社出版。
实际上,萨义德的著作一直激励着大江。1995年,那是大江获得世界性文学声誉的翌年,他再次感到笔力滞涩,陷入了短暂的彷徨。这时,萨义德的《文化与帝国主义》进入他的视野,他在《读书人》中回忆:
当时,我之所以考虑不再写小说,是因为自己的小说逐渐背离历史和现实,可以说,是钻进了自我风格的神秘主义之中,我觉得这样未免有些懒散,以致渐渐难以忍受。为批判陷于那种状态中的自我,我将《文化与帝国主义》作为恰当的批评平台。此外,以停写小说为契机,我打算与一切文学性读物断绝关系,只阅读其他领域的书籍,对于这种状态中的我来说,《文化与帝国主义》这本书完整表现出了作者丰富、开阔和高雅的世界文学作品之展望,止歇了从年轻时便浸淫于文学中的我那种无论如何也无法遏制的、对于文学书籍的饥渴。
萨义德的《文化与帝国主义》与《东方学》一起,并列为后殖民研究的里程碑式的著作。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通过大量西方小说文本,揭示了西方文化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之间的共谋关系,提供了宏阔的多元文化视角。大江为《文化与帝国主义》的丰厚而感动,他由此发现了新的航标,并意识到他的国家“主动接受文化帝国主义的统治”的现实面向。可以说,对萨义德的持续阅读和思考,使大江及其文学迈向了新的高度。
就这样,大江在《读书人》中介绍了他作为读书人的一面,读书和创作是大江生活的一体二面。大江文学与诸多书籍之间由此展现出深刻的互文关系,这也是大江与这些书籍之间的生命共振现象。威廉·布莱克诗歌的阅读体验与《新人啊,觉醒吧!》,马尔科姆·劳里作品的阅读体验与短篇小说集《倾听“雨树”的女人们》《神曲》阅读体验与《致令人眷念之年的书信》,叶芝诗歌的阅读体验与《燃烧的绿树》,爱伦·坡的《安娜贝尔·李》与《优美的安娜贝尔·李 寒彻颤栗早逝去》《晚年样式集》与萨义德的《论晚期风格:格格不入的音乐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等等,不胜枚举。然而,大江在《读书人》中提及的阅读体验只是其漫长读书生涯中的冰山一角,他在访华期间,曾经反复提及鲁迅文学的影响力。对于文体、经典、历史与现实等问题的深入思考使大江文学具有了丰富的内涵。在愈发远离文字的当下时代,大江文学还具有传承经典的一面。读书人大江的文学基于经典、传承经典,它本身也将成为经典谱系中的一分子,这也是大江文学的品质之一。